书评丨赵一菲:以商议精神激活传播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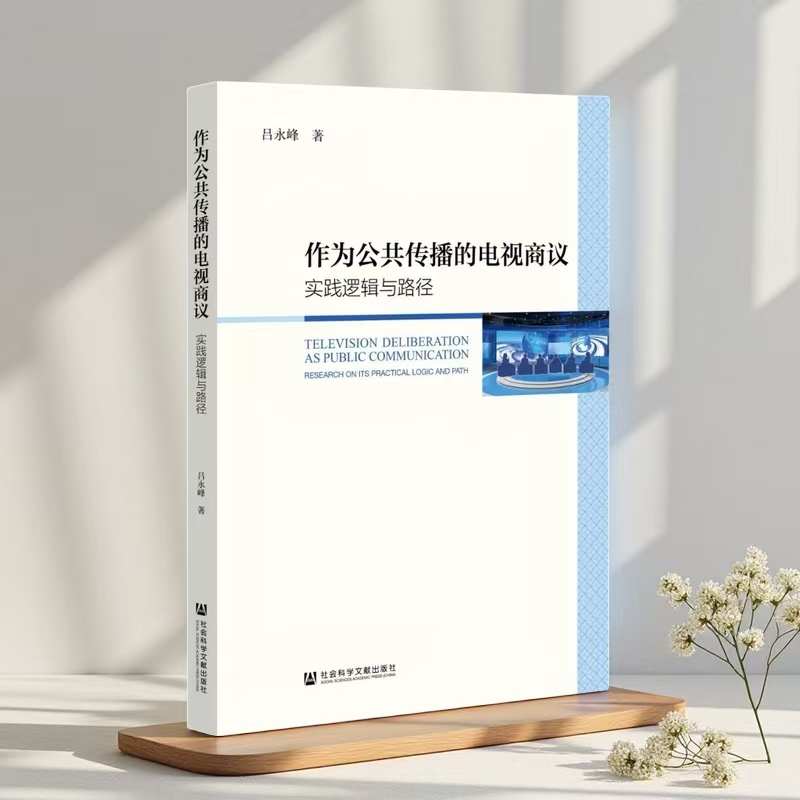
以商议精神激活传播理性
评《作为公共传播的电视商议:实践逻辑与路径》
赵一菲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当代中国构建现代化传播体系的进程中,传播不仅是信息流通的工具,更是国家治理、公共协同和社会共识的重要支撑。尤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化的传播机制增强多元主体协同、推动社会整合与治理能力提升,正成为传播学与政治学交汇处的核心议题。
吕永峰博士的新作《作为公共传播的电视商议:实践逻辑与路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正是在此语境下提出的一种兼具理论穿透力与实践指导性的公共传播方案。该书聚焦于“电视商议”这一特殊媒介现象,提出以协商逻辑重构传播制度,以公共平台承载社会治理,为公共舆论建构提供了一条面向未来的实践路径。
从表达到协商:建构制度化的公共传播路径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真正具有公共性的传播,不应止于信息表达或情绪输出,而应迈向制度化协商。这种“电视商议”模式将电视平台从单一监督工具转型为多方共议场域,推动公共传播从“看见问题”迈向“解决问题”。
作者以“传播作为制度”的视角,构建了一个五维协商模型:空间建构、主体组织、议题确认、互动规范与共识达成。这一模型不仅适用于电视类节目的流程建构,也可作为新媒体协商机制的设计参照,具备跨媒介、跨平台的适用性。它明确了协商型传播须具备的组织形式、程序规范与结果反馈机制,为媒体从“叙述中心”向“协商中介”转型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可操作路径。
这一理论转向回应了新时代舆论工作的重点任务——在信息激荡中建立理性对话机制,在观点多元中守护共识生成逻辑。
协商逻辑的制度价值:传播深度参与治理
《作为公共传播的电视商议》不仅是一部传播学研究著作,更深刻观照了制度设计的关怀。书中反复主张一个观点:协商不是弱化治理,而是治理的本质;传播不是舞台,而是平台。
书中深入分析了公共传播和电视商议的三重功能:一是作为社会整合的工具,使多元利益主体能够在对话协商中达成共识(认同或承认);二是作为治理调解的接口,将舆情转化为协商路径,减少治理成本;三是作为价值重建的平台,在对话协商中恢复社会信任。
在这一框架中,传播媒介不仅服务于党和政府的政策沟通,也通过组织对话、推动协同,成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结构中的中介环节。正如书中所言,传播的最终目标不是制造热度,而是营造协商氛围;不是显露问题,而是激发解决的能力。
回归“对话型社会”:唤醒协商文化的制度自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素有“议而后决”“众人商量”的协商传统,而本书所提出的“电视商议”正是这一文化的现代制度化演绎。它不仅重视结果达成,更注重程序的正义与表达的平权。
书中所描述的商议机制,具备四个基本特征:结构性——通过制度安排保障协商结构;普遍性——多方参与,不限身份;对话理性——强调立场表达与观点交换;协同性——以行动达成为目标。通过这些要素,公共传播平台被重构为现代协商机制的制度场域,实现从“他者发声”向“自主协同”的转型。
武汉大学单波教授评价:“吕永峰博士在本书中建立了公共传播的新实践模型,即主体间理性对话、平等协商、积极行动,在信任中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这一评价高度概括了本书的理论精髓与实践价值。
媒体治理新范式:服务全过程人民民主
本书对传播制度的设计提出了许多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操作建议,包括电视商议节目的标准化流程、参与角色的结构平衡机制、议题筛选的公共判断标准以及协商达成后的执行反馈机制等。这些制度性设计,不仅服务于特定节目制作,更可为地方媒体、行业组织、政务系统提供参考模型。
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背景下,公共传播有望成为“民主协商—媒体实践”之间的中介力量,使治理意志与公众利益在制度性程序中充分碰撞与整合。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胡正荣指出:“该书构建出逻辑自洽、科学合理的研究框架,对电视媒介参与基层社会创新治理具有较大的实践指导意义。”这一评价不仅肯定了其传播学价值,也预示其治理范式的实践意义。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 交通出行
交通出行 公积金
公积金 公安服务
公安服务 职业资格
职业资格 医疗健康
医疗健康 市场监管
市场监管 法律服务
法律服务
 融媒体平台建设服务
融媒体平台建设服务 长江云 • 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
长江云 • 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

 大数据舆情中心
大数据舆情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