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关于粮食的“烩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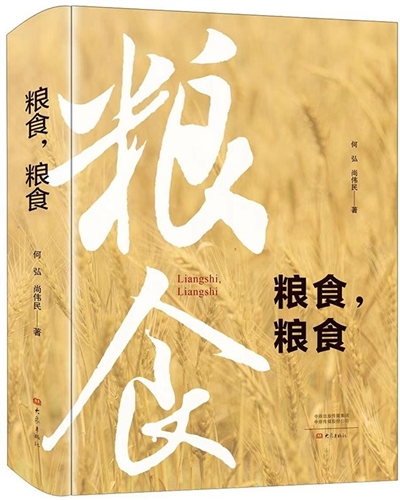
粮食问题是一个宏观的战略性问题。一个写作者来书写粮食问题,笔触可能很凝重,也可能很激愤,采用“冲上去”的姿态,很用力地抒情,或者郑重地传递情感、发表看法、作出呼吁。粮食问题本来兹事体大,采取这样的书写策略情有可原。不过,何弘与尚伟民合著的报告文学《粮食,粮食》却避开了这样的书写方式,而是通过说的方式、聊的方式,来讲述跟粮食有关的人和事。
作品开篇第一章“古人吃什么”,想象过着穷奢极欲生活的上古帝王,比如商纣,依今天的眼光看,在吃饭这件事上可谓是捉襟见肘,毫无趣味。“想拍个黄瓜,对不起,没有!想炒盘绿豆芽,对不起,没有!今天常见的蔬菜,像黄瓜、茄子、菠菜、芋头、南瓜、丝瓜、苦瓜、西红柿、扁豆、蚕豆、土豆、莴笋、花菜、卷心菜、胡萝卜等,统统没有。”可以说,从这句开始,一个聊天的“场域”就搭建起来了,整个叙事的基调就确立下来了。两处“对不起,没有”,一处“统统没有”,加上那么有耐心地罗列出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蔬菜名称,整个氛围就像是面对面沟通与交流,三五闲坐,围炉夜谈。
作品的前言部分写道,书名曾经有过很多设想,后来干脆决定用最简单的、最直接的那一个,就叫“粮食”。又考虑到粮食问题太重要了,需要加以特别的强调。如果按照“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的思路,又有点啰嗦,于是折中选了《粮食,粮食》这个书名。从拟定书名这个事上,见出写作的态度和内在的追求。作者就像是“邻家小伙”,而且是有学问、有见识的“邻家小伙”,把粮食的事娓娓道来,一二三四五,东西南北中。这就自然带来作品语言的质朴无华,语调平缓舒适,不卖弄,不硬行拼凑,读来自有味道。整部作品,起码融合了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具有博物、百科的特点;涉及历史典籍、新闻报道、专业著述、科研论文、个人回忆等,同时还融入了作者的亲身调研和个人体验,以及对有关人物的专访;既有“面”上粗线条式的俯瞰与观察,也有“点”上精细的描摹与聚焦,点面结合,编织成一张关于粮食的大网络。
在这部书里,你能了解到什么是“五谷”,了解到豫北农村“偷灯盏儿”的风俗,了解到“焦麦炸豆,小孩没娘”这则谚语有何深意,了解到“吃过大盘荆芥”这样的俗语传达着什么意思,了解到“尚超峰打井——‘泼’上了”这样的民间“典故”蕴藏着什么样的无奈,了解到杨万里居然写过“老子平生汤饼肠”这样的诗,了解到我国是第一个分离和凝固豆汁生产酪状物即豆腐、豆干的国家,了解到饥荒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惨痛回忆,了解到饥饿给人性带来怎样的沉痛考验,了解到一位中原老汉一辈子与粮食打交道的传奇经历,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解决粮食问题上有哪些革命性的部署和决定性的作为,了解到我们在超市里购买的速冻食品经历过什么样的发展历程才顺利走上亿万家庭的餐桌,了解到当下粮食安全面临什么样的严峻形势……天南海北,五花八门,汇于一炉,且烹且蒸。
说粮食、聊粮食,并不意味着把粮食的重要性和严峻性消解了。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写作语态和书写策略,是一种外在形式上的变革与探索,内里依然表达着对粮食问题的恳切关注,底色依然是热切呼唤人们节约粮食、善待粮食、重视粮食,始终保持居安思危的心态,不许有顷刻的放松与懈怠。作者把粮食问题放置在文化传统、历史长廊、国际环境、时代背景、科技变革等宏大的视野之中来审视,引导人们全方位、多角度地看待我们的饭碗问题。也就是说,这部作品的思想性、严肃性没有减损,只是通过说的方式和聊的方式,让宏大的主题变得更亲切,让人更易于沉进去,产生感触,引发思考。为何作者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讲述粮食的事?我想大概是因为粮食的事本来就跟每一个人“痛痒相关”,就是我们的烟火日常,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经手的柴米油盐,所以采用平静、缓和的叙述方式,更让人感同身受,从而击中人心,生发出深沉的共情和强劲的共鸣。写作的目的,表达的诉求,也就自然而然地实现有效的抵达。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责任编辑 夏燃)








 融媒体平台建设服务
融媒体平台建设服务 长江云 • 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
长江云 • 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

 大数据舆情中心
大数据舆情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