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退休后种树5.6万亩 他也是许多人心中的参天大树










杨善洲常说:“我手中是有权力,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
1970年,杨善洲夫人张玉珍生三女儿杨慧琴,家里缺粮,一家人靠野菜掺杂粮度日。乡民政干部经过看到这种情况,送去30斤救济大米和30斤粮票。后来杨善洲知道了,责怪张玉珍说:“我是党的干部,我们不要占公家的一点便宜,领导的家属决不能搞特殊!这大米和粮票要攒了还给公家!”差不多过了半年,张玉珍东拼西凑,才还清了这笔粮款。张玉珍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公家归公家,个人归个人,我晓得他的性格,我可以少吃点,只是娃娃们饿着可怜啊……”
因杨善洲经常“阻止”好心人对他家人的帮助,二女儿杨慧兰还曾跟他怄过气。
杨慧兰没能考上大学,想回施甸找点事情做。她报考了当地公安局,还特意给爸爸杨善洲打了电话,请他打个招呼。结果录取名单出来却没有她。原来杨善洲根本没打招呼。
后来,杨慧兰和妹妹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学校,毕业后有了固定的工作,她们的大姐杨慧菊仍然还在农村务农。
在杨善洲退休上山种树之后,他和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多了,女儿们听到老百姓对爸爸的感激和好评多了,这才渐渐理解了他。



杨善洲16岁时父亲病逝,和守寡的母亲艰难度日,母亲常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药,拿到集市上卖。是大亮山养活了他一家。
在日后风风雨雨的岁月里,杨善洲亲眼看到曾经长满大树的大亮山,一点点变秃变荒,乱砍滥伐,曾成为一个时代的隐痛。他不止一次向身边的人诉说:“都是在我们手上破坏的,一山一山都砍光了,多可惜!我们要还债!要还给下一代人一片森林、一片绿洲!”
他当地委书记期间,曾带人风餐露宿,徒步24天,详细了解大亮山的土壤、气候、地理环境,一个“种树扶贫”的梦想在他心中萌芽。
从不为家人办事、不为家乡办事的杨善洲,对家乡的人说:“退休后,我会给家乡办一两件事的!”
退休后,杨善洲婉言谢绝了按规定到昆明安家休养的厚意,说服了家人希望他回家团聚的愿望,留下一句滚烫的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说过的话就要兑现,我要回大亮山种树去!”
杨善洲带领着从各方调集的15个人,雇上18匹马,驮着被褥、锅碗瓢盆、砍刀镢头,一鼓作气上了山。
买树苗资金不足,杨善洲就经常提个口袋下山到镇里和县城的大街上去捡别人吃果子后随手扔掉的果核,桃核、梨核、龙眼核、芒果核……有什么捡什么,放在家里用麻袋装好,积少成多后用马驮上山。他说:“捡果核不出成本,省一分是一分。”
每年的端阳花节,是保山的传统节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节,杨善洲就发动全场职工,一起到街上捡果核,成了花市上一道“另类”风景。
有认识他的人说:“你一个地委书记,在大街上捡果核,多不光彩。”他说:“我这么弯弯腰,林场就有苗育了。等果子成熟了,我就光彩了!”
不过,在大街上看到父亲捡果核的女儿老二老三感到不光彩了,劝他不要再捡。他说:“是不是你们觉得丢面子了?不要老想着你们的父亲是个地委书记,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如果你们感觉我给你们丢面子了,那以后不要说我杨善洲是你们的父亲!”两个女儿流下泪水:“爸爸,我们错了……”
有一次,捡果核,杨善洲不小心撞到一个小伙子的自行车,小伙子恼了,张口就是粗话,有人赶忙把他拉一边,告诉他老人是原来的地委书记,捡果核造林呢。他惊得半天没吭声,转过身说了一句:“这样的官?我服了!”
如今,杨善洲捡回来的果核,已成为大亮山上郁郁葱葱的果林。

又是一年清明节,这是父亲逝世的第五个年头,每年的清明节以及父亲的忌日,我们全家都会邀约到善洲林场祭奠我们的父亲。回想起爸爸生前对我们姐妹及家人的“苛刻”教育,我们都已明白爸爸的“苛刻”其实是对家人最真诚的爱。他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永远烙在我的记忆深处,如同他一直都陪伴着家人和守护着他用余生创建的万亩林海。
我家住在大山里,从小就是妈妈带着我们姐妹3个和奶奶过着艰苦日子。爸爸工作忙常年在外,妈妈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家里粮食不够吃,她就上山找野菜充饥;我和妹妹没有钱上学,她就清晨上山摘野果,夜晚熬夜编粪箕、扎扫把,然后挑到街上去卖,一分一分地攒学费……那种艰难,只有妈妈心里清楚。后来,妈妈经常自豪地对我们三姐妹说:“你们三个,是我像鸟妈妈喂食一样,一口一口喂大的。”
爸爸那时虽然不常回家,但他对我们的要求却很严格。
女儿大了都要成家。在别人眼里,爸爸是地委书记,他的女儿结婚一定会非常风光隆重。但是,爸爸却要求我们姐妹三个从简办事,不让请客、不让收礼。
1968年,大姐杨惠菊结婚,爸爸寄回来30元钱,并嘱咐妈妈不准请客,不准收礼。寨邻亲戚你几毛、我一元的七拼八凑凑了45元,勉强帮着把婚事办了。
到1985年我结婚时,爸爸没有给一分钱。过了一年多我有了孩子,我一边工作,一边哺育孩子,那段时间是我最忙乱的时候。一天,爸爸突然出现在我门口,当他看到装外孙尿布的纸箱时,当即掏出100元钱给我,说:“拿去找木匠做个箱柜,把孩子的东西装好。”接过父亲给的钱,不知是委屈还是激动,眼泪流个不停。因工作调动,我搬了几次家,这柜子始终都陪着我。
从小,爸爸就教育我们:“别人的东西,即使是一分钱的也不能要。”
妹妹杨惠琴上初中时,一天遇到一位在甘蔗基地工作的阿姨,这位好心阿姨送给她3根甘蔗。对于那个时代的孩子来说,能吃上甘蔗是一件高兴的事。当妹妹拿着甘蔗跑回家正准备美美地享用时,爸爸回来了。他看见家里有甘蔗,问:“这是哪里来的?”“是农场的阿姨给的。”妹妹说。他听后脸一沉,厉声对妹妹说:“赶快送回去。不是早跟你们说过,不能要别人的东西,即使是一分钱的也不能要。”妹妹只好含着眼泪把甘蔗送了回去。
如今,我们三个姐妹都成家了,大姐已当奶奶多年了,在教育孩子上,我们仍然是遵从爸爸的教诲要求孩子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
在整理爸爸的遗物中,有一张锁在抽屉里已经发黄的“农转非”表格。在他担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按当时的政策,我的奶奶、母亲、我和三妹都可以办理“农转非”的。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填好申请表后向他报告,他却把申请表要了过去转手锁进了抽屉里。一个地委书记的母亲、老伴和三个孩子竟然在老家当农民,说起来恐怕谁都不会相信。
在爸爸晚年,我曾经问过他“农转非”的事。他告诉我说:“当时,在我们地委机关,大多数局长、科长的家属都在农村,我这个‘班长’的家属怎么能够先转呢?”
爸爸在担任地委书记期间,出差下乡时从来都不让我们搭顺风车,每次放假我从保山回家都是爸爸买好车票让我搭乘公共汽车的。公车不私用这个规矩在他上山植树造林的20年间都一直坚持。
1994年,妹妹杨惠琴即将分娩,妹夫跟爸爸说:“爸,老三快生了,有些紧张,我妈说要来看看,她年纪大了,走路不利索,还晕车,是不是请林场的车子去接一下?”爸爸说:“行,你和驾驶员去接。”可是把妈妈接来后,爸爸却掏出376元交给驾驶员,说是跑这趟车的油费、过路费,让他拿回去交给财务人员。
爸爸退休后要上大亮山植树造林的事我们一家都曾劝过。那是1987年的夏天,爸爸到学校找我们,说他要退休了,省委主要领导找他谈过话,让他到昆明安度晚年。我和爱人问他,你是怎么想的,他说:“不去”。我爱人说:“不去就不去吧!”我们都暗暗为妈妈高兴,因为爸爸工作时太忙,没有更多的时间关心和照顾妈妈,这下可好了,能给妈妈一个补偿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爸爸说他要回家乡的荒山种树。我们劝他:“你年纪大了,那个地方环境恶劣,你身体吃不消。”他说:“我在任地委书记期间,乡亲们找上门让我为家乡办点事情。我说作为保山地委书记,哪能只想着自己的家乡?我承诺过,等退休后,一定帮父老乡亲们办点实事。”我们知道劝不了他,只好告诉他到山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谁知,爸爸1988年3月退休后上大亮山种树一干就是20多年。
其实,爸爸也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无论是对群众,还是对自己的家人。1990年春节过后不久,爸爸回家看望奶奶,准备返回林场的时候,奶奶和妈妈起身送他,爸爸忽然注意到奶奶走路摇摇晃晃,赶紧放下行装,扶奶奶坐下,马上去找医生。晚上,爸爸在奶奶的屋内搭了一张小床,整夜守在奶奶身边,陪奶奶说话,给奶奶端药递水。9天后,奶奶安详地离开人世,享年89岁。
在爸爸内心深处,他觉得这一辈子对妈妈的歉疚是最多的。1996年,妈妈因胆结石住院16天,2005年因肺气肿住院13天,两次住院爸爸都从大亮山赶下来,一直守在妈妈身边。他每天早上都会买好早点,端到妈妈床前。他会在妈妈睡着后,给她扯扯被角,也会在妈妈起身时,在她身后垫个枕头。这29天,他总是一守就是一整天,我们劝他也没用。然而,爸爸生病了,却不要妈妈去看他、陪他。就在爸爸最后一次生病住院时,妈妈到医院看望他。爸爸一看见妈妈就说:“你怎么来了?你晕车,以后别来了,我不会有事的。”妈妈说:“我来看你一眼,你好了就回去。”妈妈在医院守了爸爸三天。三天里,爸爸强忍病痛折磨不出声,因为他不愿意让妈妈担心。
爸爸去世后,我们在整理他的文稿时,读到了多年来埋藏在他心里的话:“我出来工作,家庭是很困难的,家有老母亲、老伴儿,后来又有3个娃娃,就靠老伴儿在家养老供小,我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家庭……我对家庭欠债很多……我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到大亮山种树,除了想为家乡的群众做点实事,就是想离家近一点,每个月都争取回家看看。”
爸爸去世后,大姐找出了珍藏多年的爸爸买给她的白衬衫;我一遍遍抚摸着搬了几次家都舍不得扔掉的爸爸给我100元钱做的那个衣柜;妹妹想起粗心的爸爸竟然会不止一次给她买卫生用品……我们知道,爸爸是很爱我们的,只是他太忙了。他心里装着的是千千万万群众。对怀念父亲的群众来说,爸爸走了;对妈妈和我们姐妹来说,爸爸终于可以回家了,永远地回家了。如今,只要想到爸爸,我眼前浮现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参天大树。爸爸就是那棵大树,他虽然没有弯下腰,把妈妈和我们姐妹护卫在怀抱里,但是他张开双臂,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了一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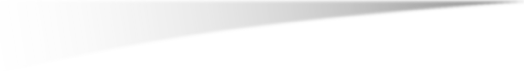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见习编辑 李小涵)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 交通出行
交通出行 公积金
公积金 公安服务
公安服务 职业资格
职业资格 医疗健康
医疗健康 市场监管
市场监管 法律服务
法律服务
 融媒体平台建设服务
融媒体平台建设服务 长江云 • 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
长江云 • 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

 大数据舆情中心
大数据舆情中心


